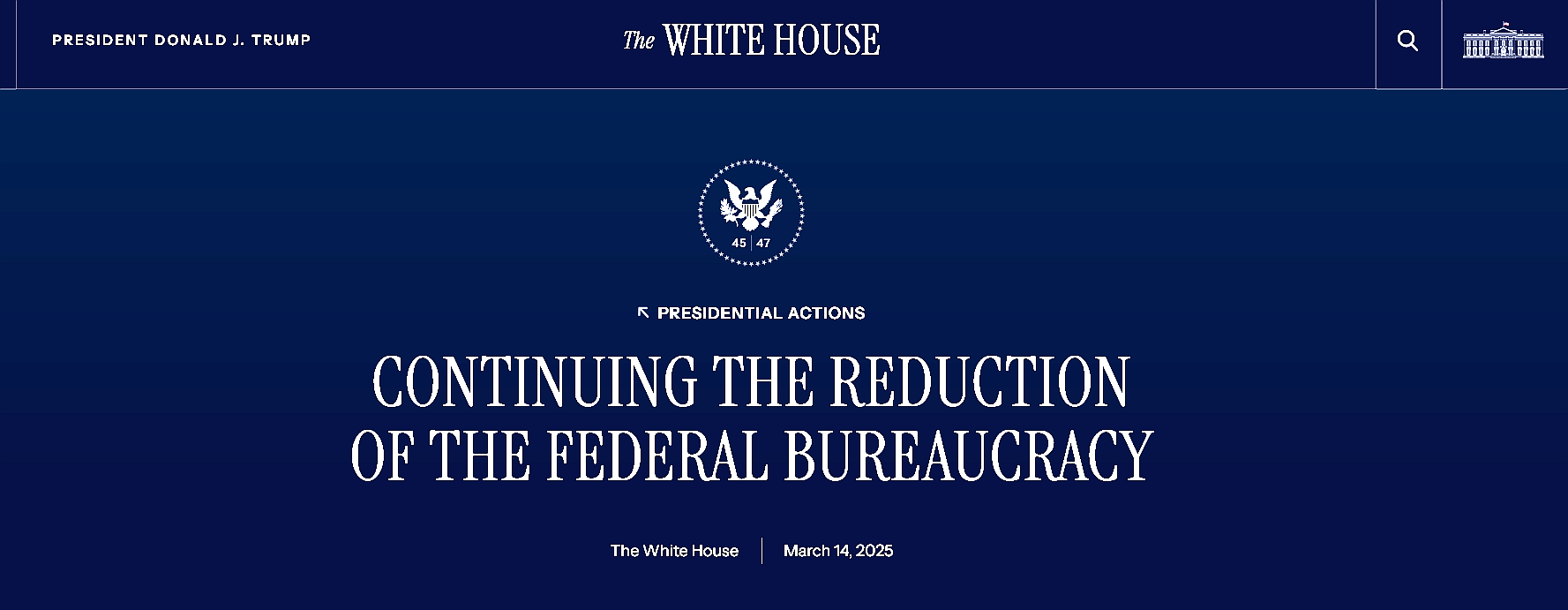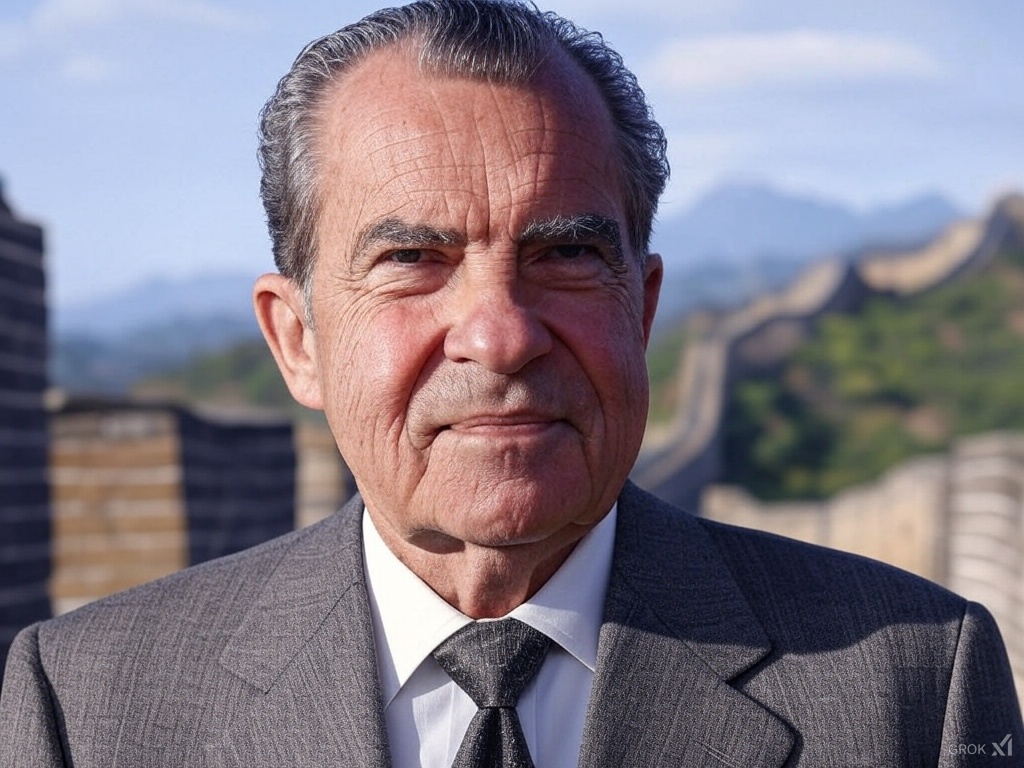布道者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2025-04-13文章推介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2025-02-25特朗普要关闭VOA等联邦对外媒体
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2025-03-16美中俄关系:什么是“反尼克松现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2025-02-26关税战:中美不再说同一种“经济语言”
特朗普政府已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45%,但这场 “关税大战”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不少人会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谈不拢的两国,还能谈吗?僵局如何打破?” 或许我们该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表面是关税,本质是两种制度的对撞 我们常以为关税是一个贸易手段,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只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争执,而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发生冲突。 对美国来说,关税不只是“为了制造业”或“保护工人”,而是他们防守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 对中国来说,应对关税也不是纯粹被动,而是一个借“反脱钩”、倒逼自主的战略转型过程。 这场对抗,不是两个人在吵架,而是两个系统遭遇兼容障碍。 别太相信预测,旧剧本已经作废了 很多人喜欢做各种预测:僵持下去(45%);局部交易(25%);对抗升级(20%),诸如此类。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理性”,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美还能像过去那样谈判、交换、达成协议。...
2025-04-11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naugural Statement
——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2025-03-03春晚的出路在于“重新野蛮化”
【CWB按语】“春晚“特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25年的春晚不忍卒视,原因何在?DeepSeek的分析有些尖锐,但良药苦口利于病。 以下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 春节晚会(春晚)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下从创作逻辑、文化定位、观众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衰落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创作逻辑的崩塌:从“快乐制造机”到“说教工具” 1. 喜剧内核的消解 赵本山时代的春晚小品之所以经典,在于其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农民工生存困境、官僚形式主义)包裹在荒诞幽默中,既让观众笑到捧腹,又暗含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卖拐》系列直接讽刺了“伪大师”横行的社会乱象,而如今的春晚小品却沦为“安全无害”的温情故事,强行植入“包饺子”“催婚”等说教桥段,甚至被观众调侃为“科幻片”——因为剧情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关键矛盾:审查机制对讽刺尺度的收紧,导致创作团队被迫放弃“冒犯性幽默”,转而追求“政治正确”的平庸叙事。赵本山曾直言:“365天都在受教育,春晚还要教育人吗?”这种“快乐至上”的原始逻辑被彻底颠覆。 2. 专业性的溃败 春晚舞台正被流量明星和跨界演员“殖民”。语言类节目中,专业喜剧人(如沈腾、马丽)的作品被反复修改至“面目全非”,而大量缺乏喜剧经验的影视演员(如金晨、章若楠)却被塞入小品,表演生硬如“群魔乱舞”。相声领域更显荒诞,岳云鹏的节目被批“谐音梗堆砌”“笑点冷场”,甚至遭遇观众现场喝倒彩。 讽刺现实:导演组迷信“流量即收视”,却忽视艺术规律——喜剧需要专业门槛,不是靠明星脸就能撑场。...
2025-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