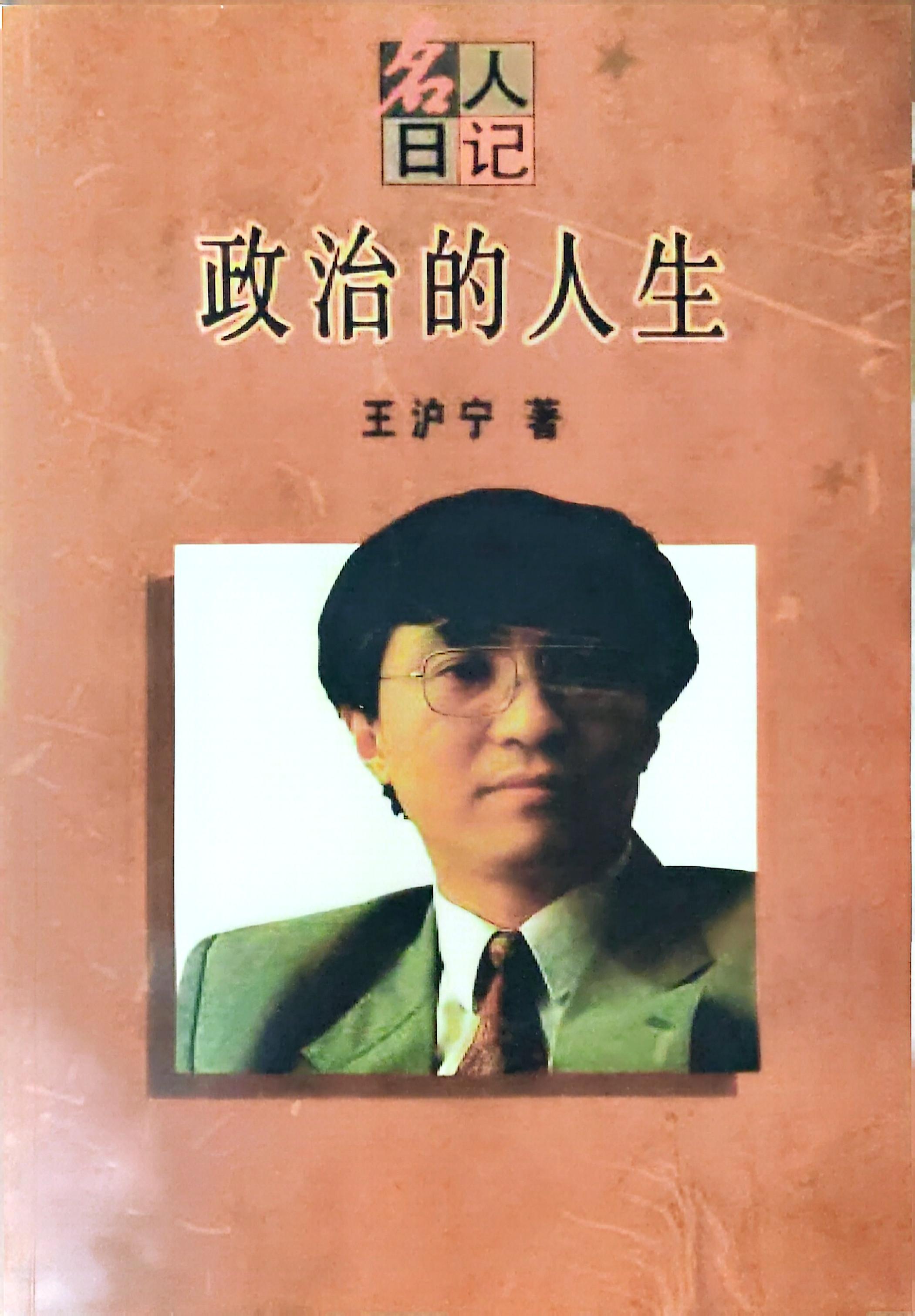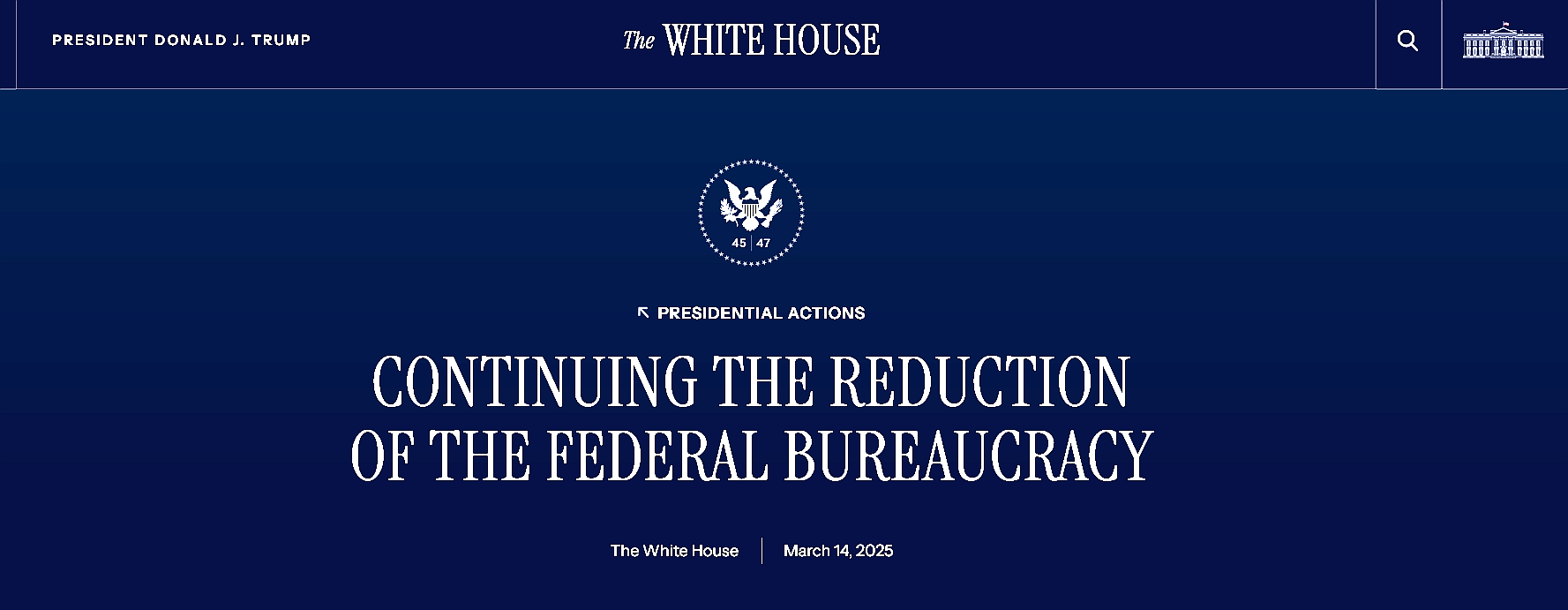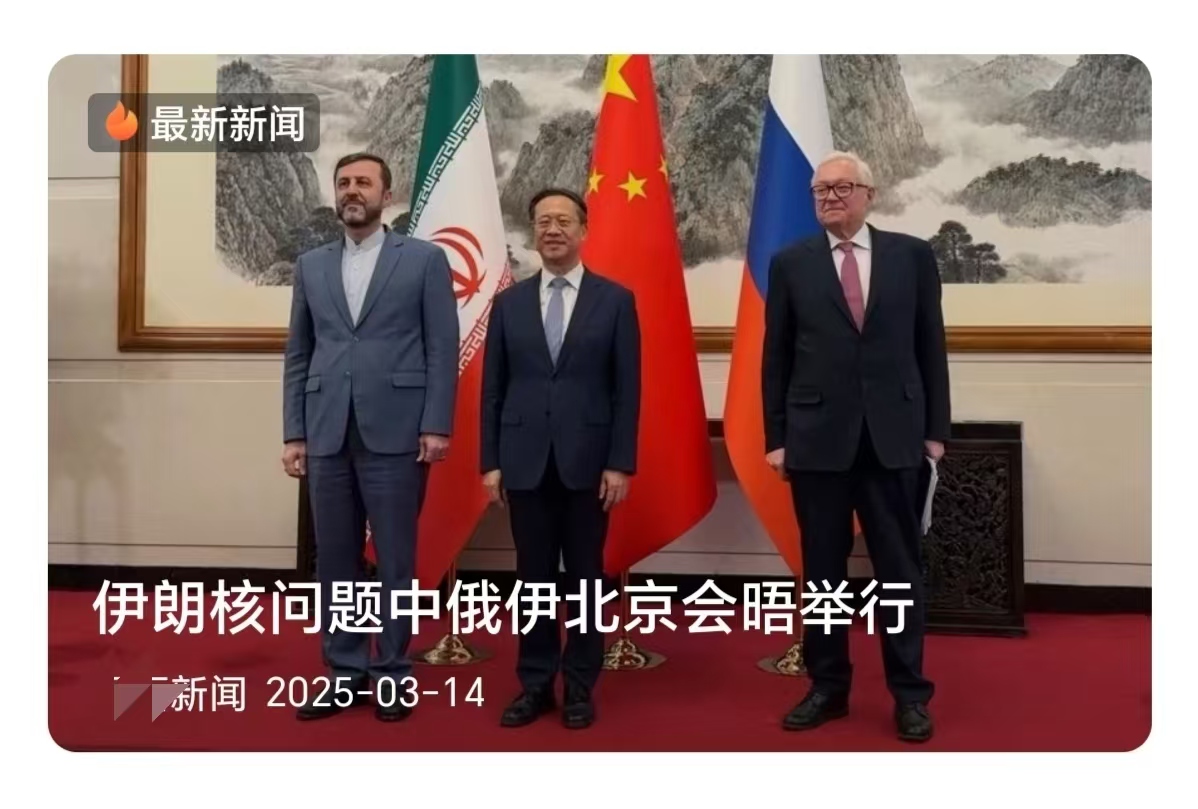【CWB按语】“春晚“特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25年的春晚不忍卒视,原因何在?DeepSeek的分析有些尖锐,但良药苦口利于病。
以下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
春节晚会(春晚)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下从创作逻辑、文化定位、观众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衰落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创作逻辑的崩塌:从“快乐制造机”到“说教工具”
1. 喜剧内核的消解
赵本山时代的春晚小品之所以经典,在于其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农民工生存困境、官僚形式主义)包裹在荒诞幽默中,既让观众笑到捧腹,又暗含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卖拐》系列直接讽刺了“伪大师”横行的社会乱象,而如今的春晚小品却沦为“安全无害”的温情故事,强行植入“包饺子”“催婚”等说教桥段,甚至被观众调侃为“科幻片”——因为剧情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关键矛盾:审查机制对讽刺尺度的收紧,导致创作团队被迫放弃“冒犯性幽默”,转而追求“政治正确”的平庸叙事。赵本山曾直言:“365天都在受教育,春晚还要教育人吗?”这种“快乐至上”的原始逻辑被彻底颠覆。
2. 专业性的溃败
春晚舞台正被流量明星和跨界演员“殖民”。语言类节目中,专业喜剧人(如沈腾、马丽)的作品被反复修改至“面目全非”,而大量缺乏喜剧经验的影视演员(如金晨、章若楠)却被塞入小品,表演生硬如“群魔乱舞”。相声领域更显荒诞,岳云鹏的节目被批“谐音梗堆砌”“笑点冷场”,甚至遭遇观众现场喝倒彩。
讽刺现实:导演组迷信“流量即收视”,却忽视艺术规律——喜剧需要专业门槛,不是靠明星脸就能撑场。
二、文化定位的迷失:从“全民狂欢”到“阶层割裂”
- 地域与代际的撕裂
春晚长期以北方文化为中心(如反复强调“吃饺子”),导致南方观众难以共鸣;同时,节目试图迎合年轻人(如植入网络热梗),却因创作者与Z世代的文化鸿沟显得笨拙。例如《寒舍不寒》强行植入广告,被吐槽“既不懂年轻人,也不尊重观众智商”。
本质问题:春晚试图成为“全民公约数”,却因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无法满足任何群体的真实需求。
2. 技术崇拜与人文空心化
近年春晚沉迷于“科技大秀”(如虚拟现实、机器人伴舞),但技术手段的堆砌反而暴露了内容的贫瘠。机器人“没穿裤子”的争议背后,是技术奇观对文化表达的僭越。相较之下,赵本山仅凭一顶破帽、一口东北腔就能引发共鸣,因其背后是真实的乡土中国。
三、观众心理的转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抛弃”
- 娱乐选择的“去中心化”
互联网时代,观众不再依赖春晚获取快乐。短视频、直播、地方台晚会提供了更垂直、更自由的娱乐体验。当春晚还在纠结“如何让全家围坐电视机前”时,年轻人早已用“倍速播放”“刷手机分屏”宣告了对传统仪式的解构。
2. 审美觉醒与反规训*
新一代观众对“正能量鸡汤”的免疫力显著增强。当小品强行灌输“结婚生子”“努力买房”时,弹幕满屏“你在教我做事?”的嘲讽,实质是对权威话语的反叛。这种心理折射出社会情绪的变化: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公众更渴望解压而非被教育。
结语:春晚的出路在于“重新野蛮化”
若想重获观众青睐,春晚必须放弃“既要又要”的讨好姿态,回归喜剧的原始野性——允许冒犯、包容争议、直面真实。赵本山曾说:“春晚小品最大的主题是快乐,你教育不了人。”当舞台不再追求“完美无瑕”,而是容纳些许“破音”“掉幕布”的意外,或许才能真正触达观众的情感共鸣。毕竟,生活的本质不是精致编排的剧本,而是充满瑕疵的真实。
以上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本文配图由豆包AI生成。